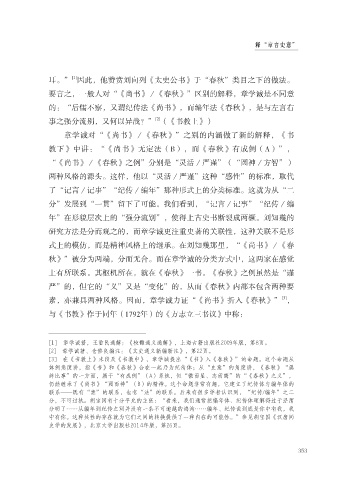Page 361 - 内文
P. 361
释“章言史意”
[1]
耳。” 因此,他赞赏刘向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目之下的做法。
要言之,一般人对“《尚书》/《春秋》”区别的解释,章学诚是不同意
的:“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
[2]
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上》)
章学诚对“《尚书》/《春秋》”之别的内涵做了新的解释,《书
教下》中讲:“《尚书》无定法(B),而《春秋》有成例(A)”,
“《尚书》/《春秋》之例”分别是“灵活/严谨”(“圆神/方智”)
两种风格的源头。这样,他以“灵活/严谨”这种“感性”的标准,取代
了“记言/记事”“纪传/编年”那种形式上的分类标准。这就为从“二
分”发展到“一贯”留下了可能。我们看到,“记言/记事”“纪传/编
年”在形貌层次上的“强分流别”,使得上古史书断裂成两橛。刘知幾的
研究方法是分而观之的,而章学诚更注重史著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是形
式上的模仿,而是精神风格上的继承。在刘知幾那里,“《尚书》/《春
秋》”被分为两端,分而无合。而在章学诚的分类方式中,这两家在感觉
上有所联系。其枢机所在,就在《春秋》一书。《春秋》之例虽然是“谨
严”的,但它的“义”又是“变化”的,从而《春秋》内部本包含两种要
[3]
素,亦兼具两种风格。因而,章学诚力证“《尚书》折入《春秋》” ,
与《书教》作于同年(1792年)的《方志立三书议》中称:
[1]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页。
[3] 在《书教上》末段及《书教中》,章学诚提出“《书》入《春秋》”的命题。这个命题从
体例角度讲,指《书》和《春秋》合在一起乃为纪传体;从“史意”的角度讲,《春秋》“属
辞比事”的一方面,属于“有成例”(A)系统,但“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之义”,
仍然继承了《尚书》“圆而神”(B)的精神。这个命题非常有趣,它建立了纪传体与编年体的
联系——既有“意”的联系,也有“法”的联系。后来有很多学者认识到,“纪传/编年”之二
分,不可过执。胡宝国有十分平允的主张:“看来,我们通常把编年体、纪传体理解得过于泾渭
分明了……从编年到纪传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编年、纪传说到底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这种共性的存在就为它们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参见胡宝国《汉唐间
史学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