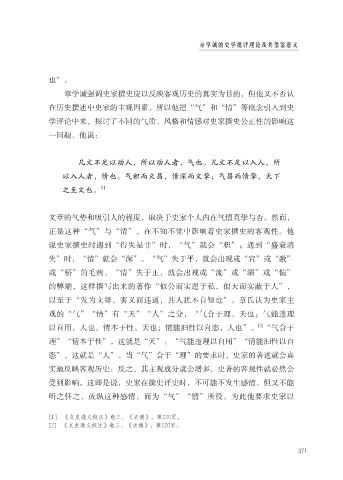Page 279 - 内文
P. 279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也”。
章学诚强调史家撰史应以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为目的,但他又不否认
在历史撰述中史家的主观因素,所以他把“气”和“情”等概念引入到史
学评论中来,探讨了不同的气质、风格和情感对史家撰史公正性的影响这
一问题。他说: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
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
之至文也。 [1]
文章的气势和吸引人的程度,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
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家撰史的客观性。他
说史家撰史时遇到“得失是非”时,“气”就会“积”;遇到“盛衰消
失”时,“情”就会“深”。“气”失于平,就会出现或“宕”或“激”
或“骄”的毛病,“情”失于正,就会出现或“流”或“溺”或“偏”
的弊端,这样撰写出来的著作“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
以至于“发为文辞,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章氏认为史家主
观的“气”“情”有“天”“人”之分,“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
[2]
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气合于
理”“情本于性”,这就是“天”:“气能违理以自用”“情能汩性以自
恣”,这就是“人”。当“气”合于“理”的要求时,史家的著述就会真
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其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就必然会
受到影响。这即是说,史家在撰史评史时,不可能不发生感情,但又不能
听之任之,放纵这种感情,而为“气”“情”所役。为此他要求史家以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20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20页。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