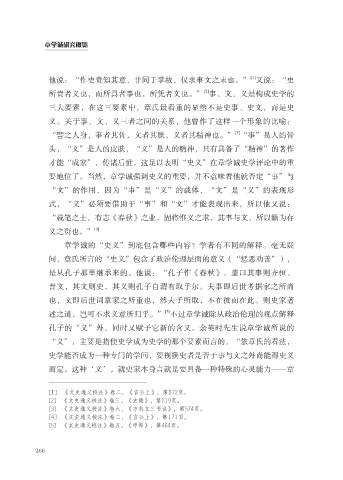Page 274 - 内文
P. 274
章学诚研究概览
[1]
他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又说:“史
[2]
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事、文、义是构成史学的
三大要素,在这三要素中,章氏最看重的显然不是史事、史文,而是史
义。关于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3]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 “事”是人的骨
头,“文”是人的皮肤,“义”是人的精神,只有具备了“精神”的著作
才能“成家”,传诸后世,这足以表明“史义”在章学诚史学评论中的重
要地位了。当然,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他就否定“事”与
“文”的作用,因为“事”是“义”的载体,“文”是“义”的表现形
式,“义”必须要借助于“事”和“文”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又说: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
义之资也。” [4]
章学诚的“史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毫无疑
问,章氏所言的“史义”包含了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惩恶劝善”),
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
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
[5]
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不过章学诚除从政治伦理的观点解释
孔子的“义”外,同时又赋予它新的含义。余英时先生说章学诚所说的
“义”,主要是指使史学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而言的,“依章氏的看法,
史学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要视撰史者是否于事与文之外尚能得史义
而定。这种‘义’,就史家本身言就是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灵能力——章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二,《言公上》,第172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第219页。
[3] 《文史通义校注》卷六,《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4] 《文史通义校注》卷二,《言公上》,第171页。
[5] 《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申郑》,第464页。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