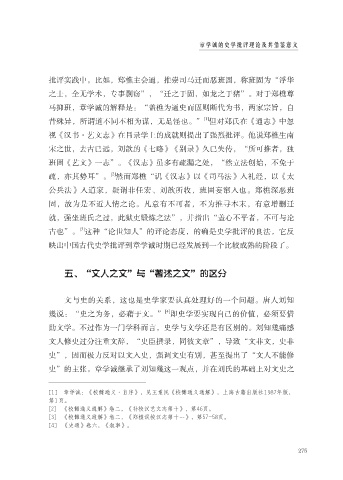Page 283 - 内文
P. 283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批评实践中。比如,郑樵主会通,推崇司马迁而恶班固,称班固为“浮华
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对于郑樵尊
马抑班,章学诚的解释是:“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
[1]
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 但对郑氏在《通志》中忽
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则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郑樵生南
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歆的《七略》《别录》久已失传,“所可推者,独
班固《艺文》一志”。《汉志》虽多有疏漏之处,“然立法创始,不免于
[2]
疏,亦其势耳”。 然而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
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
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
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并指出“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
[3]
古也”。 这种“论世知人”的评论态度,的确是史学批评的良法,它反
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到章学诚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五、“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的区分
文与史的关系,这也是史学家要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唐人刘知
[4]
幾说:“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即史学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借
助文学。不过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史学与文学还是有区别的。刘知幾痛感
文人修史过分注重文辞,“史臣撰录,同彼文章”,导致“文非文,史非
史”,因而极力反对以文入史,强调文史有别,甚至提出了“文人不能修
史”的主张。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幾这一观点,并在刘氏的基础上对文史之
[1] 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1页。
[2] 《校雠通义通解》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第46页。
[3] 《校雠通义通解》卷二,《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第57-58页。
[4] 《史通》卷六,《叙事》。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