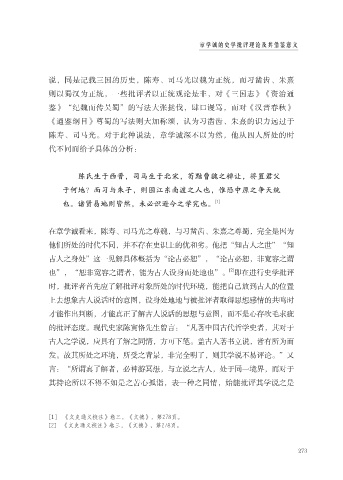Page 281 - 内文
P. 281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说,同是记载三国的历史,陈寿、司马光以魏为正统,而习凿齿、朱熹
则以蜀汉为正统,一些批评者以正统观论是非,对《三国志》《资治通
鉴》“纪魏而传吴蜀”的写法大张挞伐,肆口谩骂,而对《汉晋春秋》
《通鉴纲目》尊蜀的写法则大加称颂,认为习凿齿、朱熹的识力远过于
陈寿、司马光。对于此种说法,章学诚深不以为然,他从四人所处的时
代不同而给予具体的分析: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
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
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1]
在章学诚看来,陈寿、司马光之尊魏,与习凿齿、朱熹之尊蜀,完全是因为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不存在史识上的优和劣。他把“知古人之世”“知
古人之身处”这一见解具体概括为“论古必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
[2]
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即在进行史学批评
时,批评者首先应了解批评对象所处的时代环境,能把自己放到古人的位置
上去想象古人说话时的意图,设身处地地与被批评者取得思想感情的共鸣时
才能作出判断,才能真正了解古人说话的思想与意图,而不是心存吹毛求疵
的批评态度。现代史家陈寅恪先生曾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
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
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又
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
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
[1]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第278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德》,第278页。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