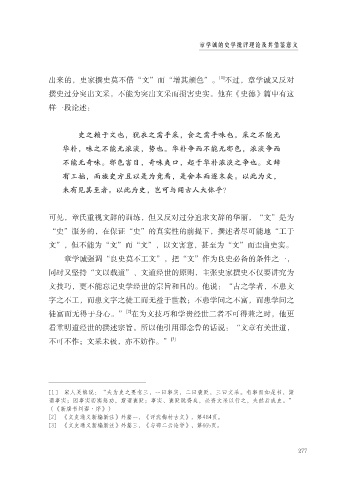Page 285 - 内文
P. 285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1]
出来的,史家撰史莫不借“文”而“增其颜色”。 不过,章学诚又反对
撰史过分突出文采,不能为突出文采而损害史实。他在《史德》篇中有这
样一段论述:
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
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
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
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
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可见,章氏重视文辞的训练,但又反对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文”是为
“史”服务的,在保证“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撰述者尽可能地“工于
文”,但不能为“文”而“文”,以文害意,甚至为“文”而歪曲史实。
章学诚强调“良史莫不工文”,把“文”作为良史必备的条件之一,
同时又坚持“文以载道”、文道经世的原则,主张史家撰史不仅要讲究为
文技巧,更不能忘记史学经世的宗旨和目的。他说:“古之学者,不患文
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无益于世教;不患学问之不富,而患学问之
[2]
徒富而无得于身心。” 在为文技巧和学贵经世二者不可得兼之时,他更
看重明道经世的撰述宗旨。所以他引用邵念鲁的话说:“文章有关世道,
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 [3]
[1] 宋人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而如是书,斯
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新唐书纠谬·序》)
[2]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评沈梅村古文》,第484页。
[3]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第665页。
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