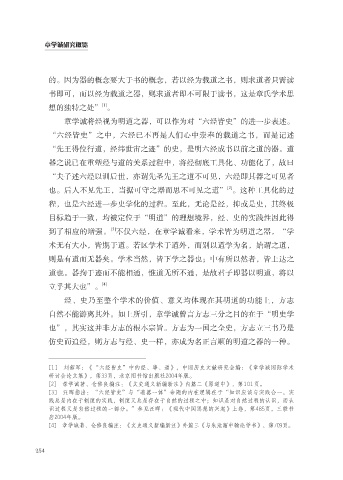Page 262 - 内文
P. 262
章学诚研究概览
的。因为器的概念要大于书的概念,若以经为载道之书,则求道者只需读
书即可,而以经为载道之器,则求道者即不可限于读书,这是章氏学术思
[1]
想的独特之处” 。
章学诚将经视为明道之器,可以作为对“六经皆史”的进一步表述。
“六经皆史”之中,六经已不再是人们心中崇奉的载道之书,而是记述
“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的史,是明六经成书以前之道的器。道
器之说已在重塑经与道的关系过程中,将经彻底工具化、功能化了,故曰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
[2]
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这种工具化的过
程,也是六经进一步史学化的过程。至此,无论是经,抑或是史,其终极
目标趋于一致,均被定位于“明道”的理想境界,经、史的实践性因此得
[3]
到了相应的增强。 不仅六经,在章学诚看来,学术皆为明道之器,“学
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
则是有道而无器矣。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
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
立乎其大也”。 [4]
经、史乃至整个学术的价值、意义均体现在其明道的功能上,方志
自然不能游离其外。如上所引,章学诚曾言方志三分之目的在于“明史学
也”,其实这并非方志的根本宗旨。方志为一国之全史,方志立三书乃是
仿史而追经,则方志与经、史一样,亦成为名正言顺的明道之器的一种。
[1] 刘韶军:《“六经皆史”中的经、事、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第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中》,第101页。
[3] 汪晖指出:“六经皆史”与“道器一体”命题的内在逻辑在于“知识应该与实践合一,实
践总是内在于制度的实践,制度又总是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之中;知识是对自然过程的认识,而认
识过程又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485页,三联书
店2004年版。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第709页。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