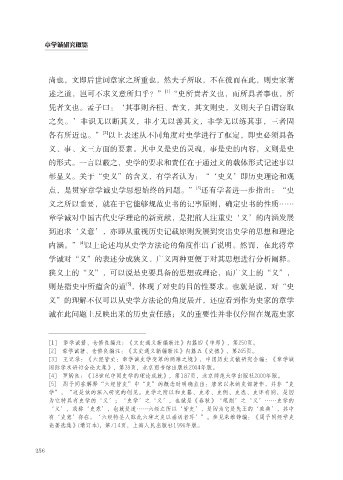Page 264 - 内文
P. 264
章学诚研究概览
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
[1]
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
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
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
[2]
各有所近也。” 以上表述从不同角度对史学进行了框定,即史必须具备
义、事、文三方面的要素。其中义是史的灵魂,事是史的内容,文则是史
的形式。一言以蔽之,史学的要求和责任在于通过文的载体形式记述事以
彰显义。关于“史义”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
[3]
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史
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规范史书的记事原则,确定史书的性质……
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新贡献,是把前人注重史‘义’的内涵发展
到追求‘义意’,亦即从重视历史记载原则发展到突出史学的思想和理论
[4]
内涵。” 以上论述均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作出了说明。然而,在此将章
学诚对“义”的表述分成狭义、广义两种更便于对其思想进行分析阐释。
狭义上的“义”,可以说是史要具备的思想或理论,而广义上的“义”,
[5]
则是指史中所蕴含的道 ,体现了对史的目的性要求。也就是说,对“史
义”的理解不仅可以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展开,还应看到作为史家的章学
诚在此问题上反映出来的历史责任感;义的重要性并非仅停留在规范史家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申郑》,第250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五《史德》,第265页。
[3] 王记录:《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4] 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第18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周予同在解释“六经皆史”中“史”的概念时明确点出: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并非“史
学”,“这是他的深入研究的创见。史学之所以和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有别,是因
为它特具有史学的‘义’;‘史学’之‘义’,也就是《春秋》‘笔削’之‘义’……史学的
‘义’,或称‘史意’,也就是道……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它是先王的‘政典’,其中
有‘史意’存在,‘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