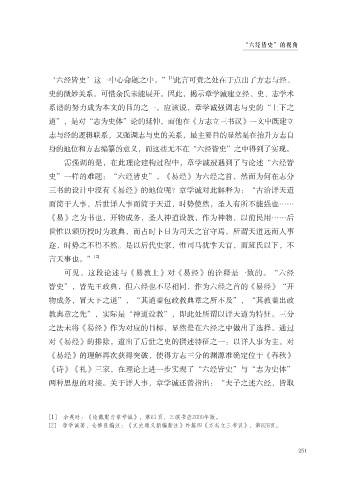Page 259 - 内文
P. 259
“六经皆史”的视角
[1]
‘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 此言可贵之处在于点出了方志与经、
史的微妙关系,可惜余氏未能展开。因此,揭示章学诚建立经、史、志学术
系谱的努力成为本文的目的之一。应该说,章学诚强调志与史的“上下之
道”,是对“志为史体”论的延伸,而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既建立
志与经的逻辑联系,又强调志与史的关系,最主要目的显然是在抬升方志自
身的地位和方志编纂的意义,而这些无不在“六经皆史”之中得到了实现。
需强调的是,在此理论建构过程中,章学诚遭遇到了与论述“六经皆
史”一样的难题:“六经皆史”,《易经》为六经之首,然而为何在志分
三书的设计中没有《易经》的地位呢?章学诚对此解释为:“古治详天道
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
《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后
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
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
言天事也。” [2]
可见,这段论述与《易教上》对《易经》的诠释是一致的。“六经
皆史”,皆先王政典,但六经也不尽相同,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开
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
教典章之先”,实际是“神道设教”,即此处所谓以详天道为特征。三分
之法未将《易经》作为对应的目标,显然是在六经之中做出了选择。通过
对《易经》的排除,道出了后世之史的撰述特征之一:以详人事为主。对
《易经》的理解再次获得突破,使得方志三分的渊源准确定位于《春秋》
《诗》《礼》三家,在理论上进一步实现了“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
两种思想的对接。关于详人事,章学诚还曾指出:“夫子之述六经,皆取
[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1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8页。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