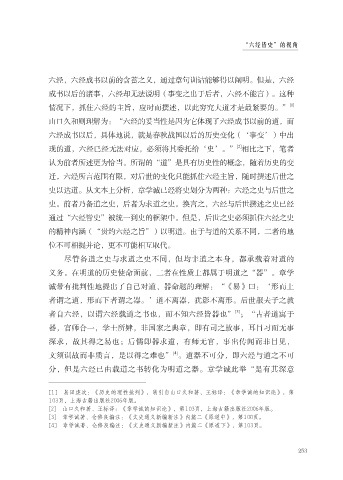Page 261 - 内文
P. 261
“六经皆史”的视角
六经,六经成书以前的含蓄之义,通过章句训诂能够得以阐明。但是,六经
成书以后的诸事,六经却无法说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这种
情况下,抓住六经的主旨,应时而撰述,以此穷究大道才是最紧要的。” [1]
山口久和则理解为:“六经的妥当性是因为它体现了六经成书以前的道,而
六经成书以后,具体地说,就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变化(‘事变’)中出
[2]
现的道,六经已经无法对应,必须将其委托给‘史’。” 相比之下,笔者
认为前者所述更为恰当。所谓的“道”是具有历史性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变
迁,六经所言范围有限,对后世的变化只能抓住六经主旨,随时撰述后世之
史以达道。从文本上分析,章学诚已经将史划分为两种:六经之史与后世之
史。前者乃备道之史,后者为求道之史。换言之,六经与后世撰述之史已经
通过“六经皆史”被统一到史的框架中。但是,后世之史必须抓住六经之史
的精神内涵(“贵约六经之旨”)以明道。由于与道的关系不同,二者的地
位不可相提并论,更不可能相互取代。
尽管备道之史与求道之史不同,但均非道之本身,都承载着对道的
义务。在明道的历史使命面前,二者在性质上都属于明道之“器”。章学
诚带有批判性地提出了自己对道、器命题的理解:“《易》曰:‘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
[3]
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古者道寓于
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
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
[4]
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 。道器不可分,即六经与道之不可
分,但是六经已由载道之书转化为明道之器。章学诚此举“是有其深意
[1] 岛田虔次:《历史的理性批判》,转引自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第
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中》,第100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原道下》,第103页。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