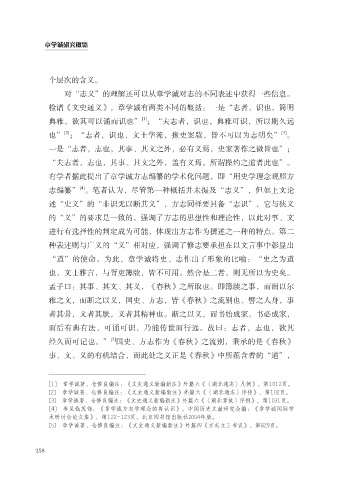Page 266 - 内文
P. 266
章学诚研究概览
个层次的含义。
对“志义”的理解还可以从章学诚对志的不同表述中获得一些信息。
检诸《文史通义》,章学诚有两类不同的概括:一是“志者,识也,简明
[1]
典雅,欲其可以诵而识也” ;“夫志者,识也,典雅可识,所以期久远
[3]
[2]
也” ;“志者,识也,文士华藻,掾史案牍,皆不可以为志明矣” 。
一是“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
“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
有学者据此提出了章学诚方志编纂的学术化问题,即“用史学理念观照方
[4]
志编纂” 。笔者认为,尽管第一种概括并未提及“志义”,但如上文论
述“史义”的“非识无以断其义”,方志同样要具备“志识”,它与狭义
的“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强调了方志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以此对事、文
进行有选择性的判定成为可能,体现出方志作为撰述之一种的特点。第二
种表述则与广义的“义”相对应,强调了修志要承担在以文言事中彰显出
“道”的使命。为此,章学诚将史、志作出了形象的比喻:“史之为道
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
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
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
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
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
[5]
经久而可记也。” 国史、方志作为《春秋》之流别,秉承的是《春秋》
事、文、义的有机结合,而此处之义正是《春秋》中所蕴含着的“道”,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湖北通志〉凡例》,第1012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湖北通志〉序传》,第102页。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湖北掌故〉序例》,第1031页。
[4] 参见钱茂伟:《章学诚方志学理念的再认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2-12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5]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9页。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