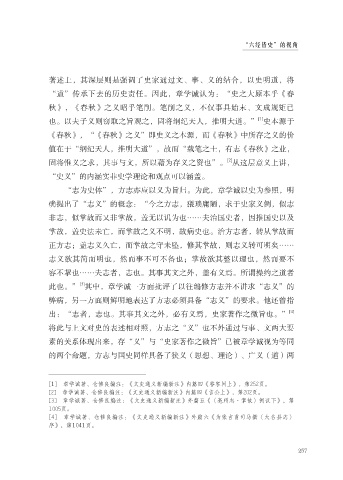Page 265 - 内文
P. 265
“六经皆史”的视角
著述上,其深层则是强调了史家通过文、事、义的结合,以史明道,将
“道”传承下去的历史责任。因此,章学诚认为:“史之大原本乎《春
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
[1]
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史本源于
《春秋》,“《春秋》之义”即史义之本源,而《春秋》中所存之义的价
值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故而“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
[2]
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 从这层意义上讲,
“史义”的内涵实非史学理论和观点可以涵盖。
“志为史体”,方志亦应以义为旨归。为此,章学诚以史为参照,明
确提出了“志义”的概念:“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
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
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
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
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
容不挈也……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
[3]
此也。” 其中,章学诚一方面批评了以往编修方志并不讲求“志义”的
弊病,另一方面则鲜明地表达了方志必须具备“志义”的要求。他还曾指
出:“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 [4]
将此与上文对史的表述相对照,方志之“义”也不外通过与事、文两大要
素的关系体现出来,存“义”与“史家著作之微旨”已被章学诚视为等同
的两个命题,方志与国史同样具备了狭义(思想、理论)、广义(道)两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答客问上》,第252页。
[2]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言公上》,第202页。
[3]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下》,第
1005页。
[4]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
序》,第1041页。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