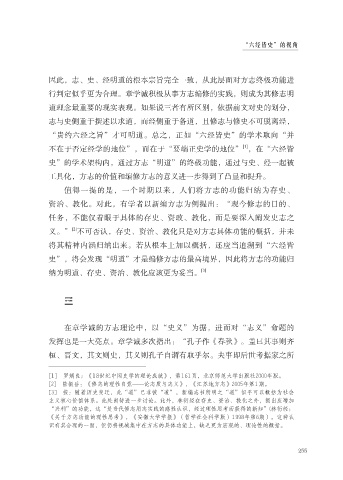Page 263 - 内文
P. 263
“六经皆史”的视角
因此,志、史、经明道的根本宗旨完全一致,从此层面对方志终极功能进
行判定似乎更为合理。章学诚积极从事方志编修的实践,则成为其修志明
道理念最重要的现实表现。如果说三者有所区别,依据前文对史的划分,
志与史侧重于撰述以求道,而经侧重于备道,且修志与修史不可脱离经,
“贵约六经之旨”才可明道。总之,正如“六经皆史”的学术取向“并
[1]
不在于否定经学的地位”,而在于“要端正史学的地位” ,在“六经皆
史”的学术架构内,通过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通过与史、经一起被
工具化,方志的价值和编修方志的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凸显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将方志的功能归纳为存史、
资治、教化。对此,有学者以新编方志为例提出:“现今修志的目的、
任务,不能仅着眼于具体的存史、资政、教化,而是要深入阐发史志之
[2]
义。” 不可否认,存史、资治、教化只是对方志具体功能的概括,并未
将其精神内涵归纳出来。若从根本上加以概括,还应当追溯到“六经皆
史”,将会发现“明道”才是编修方志的最高境界,因此将方志的功能归
纳为明道、存史、资治、教化应该更为妥当。 [3]
三
在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中,以“史义”为据,进而对“志义”命题的
发挥也是一大亮点。章学诚多次指出:“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
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
[1] 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第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陆振岳:《修志的理性自觉——论志质与志义》,《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1期。
[3] 按:随着历史变迁,此“道”已非彼“道”,新编志书所明之“道”似乎可以概括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处尚待进一步讨论。此外,林衍经在存史、资治、教化之外,提出应增加
“兴利”的功能,这“是当代修志用志实践的感性认识,经过理性思考而获得的新知”(林衍经:
《关于方志功能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这种认
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仍将视域集中在方志的具体功能上,缺乏更为宏观的、理论性的概括。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