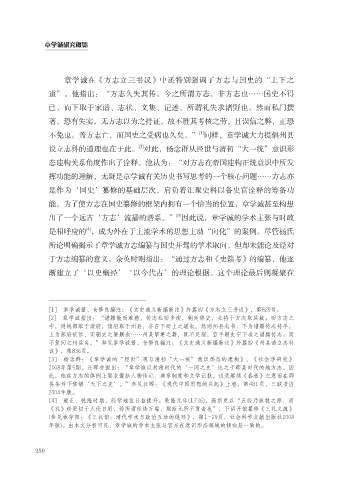Page 258 - 内文
P. 258
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还特别强调了方志与国史的“上下之
道”。他指出:“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国史不得
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
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
[1]
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 同样,章学诚大力提倡州县
[2]
设立志科的道理也在于此。 对此,杨念群从经世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
态建构关系角度作出了诠释。他认为:“对方志在帝国建构正统意识中所发
挥功能的理解,无疑是章学诚有关历史书写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方志亦
是作为‘国史’纂修的基础层次,肩负着汇聚史料以备史官诠释的筹备功
能,为了使方志在国史纂修的框架内拥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章学诚甚至构想
[3]
出了一个远古‘方志’流播的谱系。” 因此说,章学诚的学术主张与时政
[4]
是相呼应的 ,成为外在于主流学术的思想主动“向化”的案例。尽管杨氏
所论明确揭示了章学诚方志编纂与国史并驾的学术取向,但却未能论及经对
于方志编纂的意义。余英时则指出:“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
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
[1]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第829页。
[2] 章学诚指出:“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
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
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
不复问之州县矣。”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州县请立志科
议》,第836页。
[3] 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
2008年第5期。汪晖亦提出:“章学诚以封建时代的‘一国之史’比之于郡县时代的地方志。因
此,他在方志的体例上要求囊括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和文学记载。这是赓续《春秋》之意而在郡
县条件下修缮‘天下之史’。”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481页,三联书店
2004年版。
[4] 雍正、乾隆时期,经学地位日益提升。乾隆元年(1736),高宗更以“五经乃政教之原,而
《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下诏开馆纂修《三礼义疏》
(参见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第1-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由本文分析可见,章学诚的学术主张与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是一致的。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