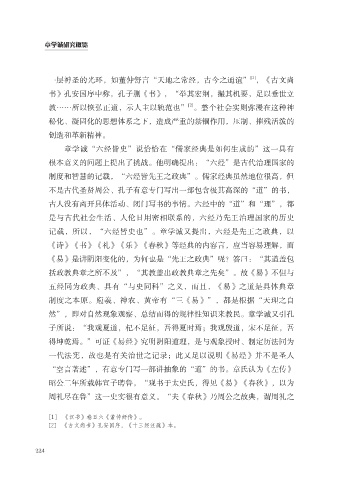Page 232 - 内文
P. 232
章学诚研究概览
[1]
一层神圣的光环,如董仲舒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古文尚
书》孔安国序中称,孔子删《书》,“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
[2]
教……所以恢弘正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整个社会实则弥漫在这种神
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造成严重的禁锢作用,压制、摧残活泼的
创造和革新精神。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恰恰在“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具有
根本意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挑战。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
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
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有意专门写出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
古人没有离开具体活动、闭门写书的事情。六经中的“道”和“理”,都
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相联系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
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章学诚又提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以
《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内容言,应当容易理解,而
《易》是讲阴阳变化的,为何也是“先王之政典”呢?答曰:“其道盖包
括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故《易》不但与
五经同为政典、具有“与史同科”之义,而且,《易》之道是具体典章
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
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的规律性知识来教民。章学诚又引孔
子所说:“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
得坤乾焉。”可证《易经》究明阴阳道理,是与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同为
一代法宪,故也是有关治世之记录;此又足以说明《易经》并不是圣人
“空言著述”,有意专门写一部讲抽象的“道”的书。章氏认为《左传》
昭公二年所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春秋》,以为
周礼尽在鲁”这一史实很有意义。“夫《春秋》乃周公之故典,谓周礼之
[1]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 《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十三经注疏》本。
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