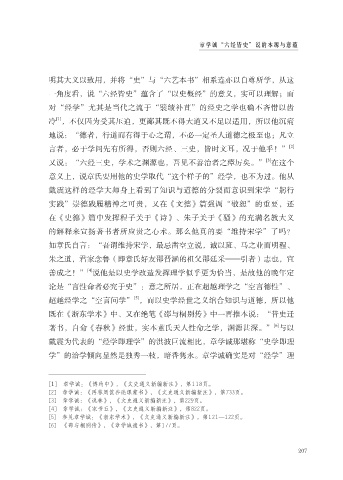Page 215 - 内文
P. 215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明其大义以致用,并将“史”与“六艺本书”相系连亦以自尊所学,从这
一角度看,说“六经皆史”蕴含了“以史概经”的意义,实可以理解;而
对“经学”尤其是当代之流于“襞绩补苴”的经史之学也确不吝惜以齿
[1]
冷 ,不仅因为受其压迫,更鄙其既不得大道又不足以适用,所以他沉痛
地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不必一定圣人道德之极至也;凡立
言者,必于学问先有所得,否则六经、三史,皆时文耳,况于他乎!” [2]
[3]
又说:“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在这个
意义上,说章氏要用他的史学取代“这个样子的”经学,也不为过。他从
戴震这样的经学大师身上看到了知识与道德的分裂而意识到宋学“躬行
实践”崇德践履精神之可贵,又在《文德》篇强调“敬恕”的重要,还
在《史德》篇中发挥程子关于《诗》、朱子关于《骚》的充满名教大义
的解释来宣扬著书者所应贵之心术。那么他真的要“维持宋学”了吗?
如章氏自言:“吾谓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
朱之道,君家念鲁(即章氏好友邵晋涵的祖父邵廷采——引者)志也,宜
[4]
善成之!” 说他是以史学改造发挥理学似乎更为恰当,是故他的晚年定
论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意之所居,正在超越理学之“空言德性”、
[5]
超越经学之“空言问学” ,而以史学经世之义绾合知识与道德,所以他
既在《浙东学术》中、又在绝笔《邵与桐别传》中一再推本说:“昔史迁
[6]
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甚深。” 与以
戴震为代表的“经学即理学”的洪波巨流相比,章学诚那堪称“史学即理
学”的治学倾向显然是独秀一枝,暗香隽永。章学诚确实是对“经学”理
[1] 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18页。
[2] 章学诚:《再答周筤谷论课蒙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33页。
[3] 章学诚:《说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29页。
[4] 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2页。
[5] 参见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21—122页。
[6] 《邵与桐别传》,《章学诚遗书》,第177页。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