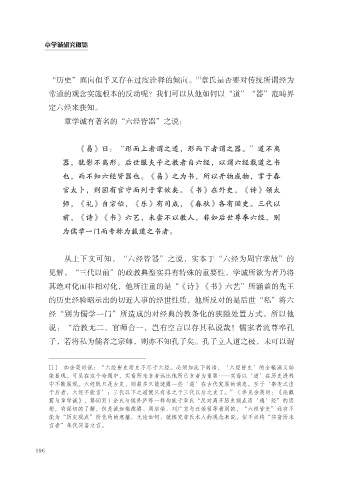Page 204 - 内文
P. 204
章学诚研究概览
[1]
“历史”面向似乎又存在过度诠释的倾向。 章氏是否要对传统所谓经为
常道的观念实施根本的反动呢?我们可以从他如何以“道”“器”范畴界
定六经来获知。
章学诚有著名的“六经皆器”之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
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
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物,掌于春
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太
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
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
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从上下文可知,“六经皆器”之说,实本于“六经为周官掌故”的
见解。“三代以前”的政教典型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诚所欲为者乃将
其绝对化而非相对化,他所注重的是“《诗》《书》六艺”所涵盖的先王
的历史经验昭示出的切近人事的经世性质,他所反对的是后世“私”将六
经“别为儒学一门”所造成的对经典的教条化的狭隘处置方式。所以他
说:“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
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未可以谓
[1] 如余英时说:“六经皆史而史不尽于六经。必须如此下转语,‘六经皆史’的全幅涵义始
能显现。可见在这个命题中,实斋所未言者远比他所已言者为重要……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
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
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参见余英时:《论戴
震与章学诚》,第60页)余氏与侯外庐等一样均能于章氏“反对离开历史观点而‘通’经”的思
想,有深切的了解,但是诚如柴德赓、周启荣、刘广京与汪荣祖等看到的,“六经皆史”还有不
能为“历史观点”所化约的意蕴,无论如何,就探究章氏本人的观念来说,似不必将“实斋所未
言者”来代实斋立言。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