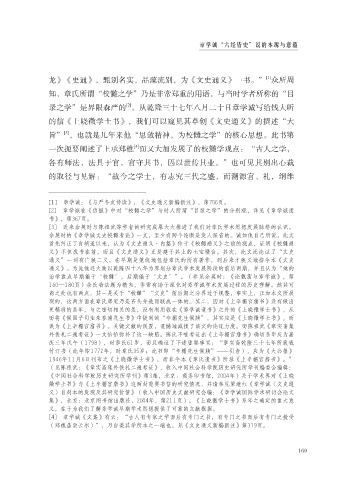Page 177 - 内文
P. 177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1]
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众所周
知,章氏所谓“校雠之学”乃是非常郑重的用语,与当时学者所称的“目
[2]
录之学”是界限森严的 。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章学诚写给钱大昕
的信《上晓徵学士书》,我们可以窥见其草创《文史通义》的撰述“大
[3]
旨” ,也就是几年来他“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的核心思想。此书第
[4]
一次扼要阐述了上承郑樵 而又大加发展了的校雠学观点:“古人之学,
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也可见其别出心裁
的取径与见解:“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
[1] 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2] 章学诚在《信摭》中对“校雠之学”与时人所谓“目录之学”的分别观,详见《章学诚遗
书》,第367页。
[3] 近来余英时与陈祖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章氏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
余英时的《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至少有两个论断是发人深省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此文
首先纠正了自胡适以来,认为《文史通义·内篇》作于《校雠通义》之前的观点,证明《校雠通
义》不但成书在前,而且《文史通义》正是建于其上的七宝楼台。其次,此文还论证了“文史
通义”一词有广狭二义。在早期是笼统地包括章氏的所有著作,到后来才狭义地指今本《文史
通义》。为此他还大致以乾隆四十八年为界划分章氏学术发展阶段的前后两期,并且认为“他的
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后期偏于‘文史’”。(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
160—180页)余氏看法颇为精当,非常有助于深化对章学诚学术发展过程的历史理解。然其可
商之处也有两点,其一是关于“校雠”“文史”前后期之分界过于规整,事实上,正如本文所展
现的,这两方面在章氏那里乃是齐头并进而联成一体的。其二,因对《上辛楣宫詹书》没有做出
更精准的系年,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利用收在《章学诚遗书》之外的《上晓徵学士书》,从
而将《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提到的“辛楣先生候牍”,其实应是《上晓徵学士书》,而
误为《上辛楣宫詹书》。关键文献的误置,遗憾地减损了该文的论证力度。而陈祖武《章实斋集
外佚札二通考证》一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陈氏不唯考证出《上辛楣宫詹书》确切系年应为嘉
庆三年戊午(1798),时章氏61岁,而且确证了下述重要事实:“章实斋乾隆三十七年所致钱
竹汀书(此年即1772年,时章氏35岁;此书即“辛楣先生候牍”——引者),应为《大公报》
1946年11月6日刊布之《上晓徵学士书》,而非今本《章氏遗书》所录《上辛楣宫詹书》。”
(见陈祖武:《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关于学术界对《上晓
徵学士书》与《上辛楣宫詹书》这两封重要书信的研究情况,并请参见梁继红《章学诚〈文史通
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上晓徵学士书》系年之确定的重大意
义,在于为我们了解章学诚早期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根据。
[4] 章学诚《文集》有云:“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
(郑樵盖尝云尔)”,乃自道其学所本之一端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