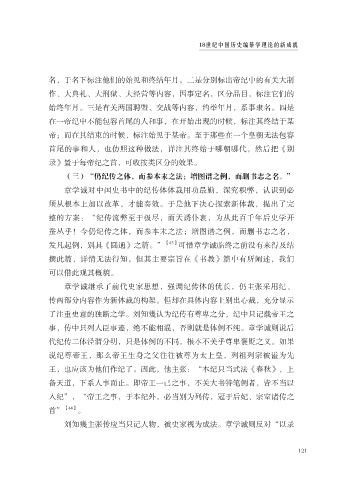Page 129 - 内文
P. 129
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名,于名下标注他们的始见和终结年月。二是分别标出帝纪中的有关大制
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等内容,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标注它们的
始终年月。三是有关两国聘盟、交战等内容,约举年月,系事隶名。四是
在一帝纪中不能包容首尾的人和事,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标注其终结于某
帝;而在其结束的时候,标注始见于某帝。至于那些在一个皇朝无法包容
首尾的事和人,也仿照这种做法,详注其终始于哪朝哪代,然后把《别
录》置于每帝纪之首,可收按类区分的效果。
(三)“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
章学诚对中国史书中的纪传体体裁用功最勤,深究积弊,认识到必
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才能奏效。于是他下决心探索新体裁,提出了完
整的方案:“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
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
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 【43】 可惜章学诚临终之前没有来得及结
撰此篇,详情无法得知。但其主要宗旨在《书教》篇中有所阐述,我们
可以借此观其概貌。
章学诚继承了前代史家思想,强调纪传体的优长,仍主张采用纪、
传两部分内容作为新体裁的构架。但却在具体内容上别出心裁,充分显示
了注重史意的独断之学。刘知幾认为纪传有尊卑之分,纪中只记载帝王之
事,传中只列人臣事迹,绝不能相混,否则就是体例不纯。章学诚则说后
代纪传二体泾渭分明,只是体例的不同,根本不关乎尊卑褒贬之义。如果
说纪尊帝王,那么帝王生身之父往往被尊为太上皇,列祖列宗被谥为先
王,也应该为他们作纪了。因此,他主张:“本纪只当式法《春秋》,上
备天道,下系人事而止。即帝王一己之事,不关大书特笔例者,皆不当以
入纪”,“帝王之事,于本纪外,必当别为列传,冠于后妃、宗室诸传之
首” 【44】 。
刘知幾主张传应当只记人物,被史家视为成法。章学诚则反对“以录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