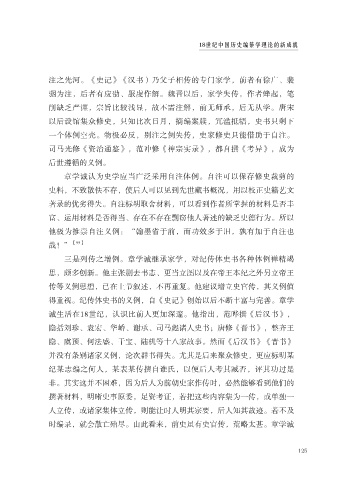Page 133 - 内文
P. 133
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注之先河。《史记》《汉书)乃父子相传的专门家学,前者有徐广、裴
骃为注,后者有应劭、服虔作解。魏晋以后,家学失传,作者蜂起,笔
削缺乏严谨,宗旨比较浅显,故不需注解,前无师承,后无从学。唐宋
以后设馆集众修史,只知比次日月,摘编案牍,冗滥抵牾,史书只剩下
一个体例空壳。物极必反,别注之例失传,史家修史只能借助于自注。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范冲修《神宗实录》,都自撰《考异》,成为
后世遵循的义例。
章学诚认为史学应当广泛采用自注体例。自注可以保存修史裁剪的
史料,不致散佚不存,使后人可以见到先世藏书概况,用以校正史籍艺文
著录的优劣得失。自注标明取舍材料,可以看到作者所掌握的材料是否丰
富、运用材料是否得当、存在不存在剽窃他人著述的缺乏史德行为。所以
他极为推崇自注义例:“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
哉!” 【55】
三是列传之增例。章学诚继承家学,对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禅精竭
思,颇多创新。他主张删去书志、更当立图以及在帝王本纪之外另立帝王
传等义例思想,已在上节叙述,不再重复。他建议增立史官传,其义例值
得重视。纪传体史书的义例,自《史记》创始以后不断丰富与完善。章学
诚生活在18世纪,认识比前人更加深邃。他指出,范晔撰《后汉书》,
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人史书;唐修《晋书》,整齐王
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等十八家故事。然而《后汉书》《晋书》
并没有条别诸家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尤其是后来聚众修史,更应标明某
纪某志编之何人,某表某传撰自谁氏,以便后人考其臧否,评其功过是
非。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人为前朝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
撰著材料,明晰史事原委,足资考证,若把这些内容集为一传,或单独一
人立传,或诸家集体立传,则能让时人明其宗要,后人知其故迹。若不及
时编录,就会散亡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官传,荒略太甚。章学诚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