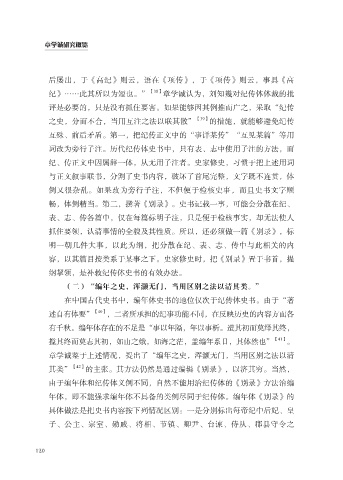Page 128 - 内文
P. 128
章学诚研究概览
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
纪》……此其所以为短也。” 【38】 章学诚认为,刘知幾对纪传体体裁的批
评是必要的,只是没有抓住要害。如果能够因其例推而广之,采取“纪传
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 【39】 的措施,就能够避免纪传
互殊、前后矛盾。第一,把纪传正文中的“事详某传”“互见某篇”等用
词改为旁行子注。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只有表、志中使用子注的方法,而
纪、传正文中因属辞一体,从无用子注者。史家修史,习惯于把上述用词
与正文叙事联书,分割了史书内容,破坏了首尾完整,文字既不连贯,体
例又很杂乱。如果改为旁行子注,不但便于检核史事,而且史书文字顺
畅,体例精当。第二,撰著《别录》。史书记载一事,可能会分散在纪、
表、志、传各篇中,仅在每篇标明子注,只是便于检核事实,却无法使人
抓住要领,认清事情的全貌及其性质。所以,还必须做一篇《别录》,标
明一朝几件大事,以此为纲,把分散在纪、表、志、传中与此相关的内
容,以其篇目按类系于某事之下。史家修史时,把《别录》置于书首,提
纲挈领,是补救纪传体史书的有效办法。
(二)“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仅次于纪传体史书。由于“著
述自有体要” 【40】 ,二者所承担的纪事功能不同,在反映历史的内容方面各
有千秋。编年体存在的不足是“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而莫绎其终,
揽其终而莫志其初,如山之娥,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41】 。
章学诚鉴于上述情况,提出了“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
其类” 【42】 的主张。其方法仍然是通过编辑《别录》,以济其穷。当然,
由于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不同,自然不能用治纪传体的《别录》方法治编
年体,即不能强求编年体不具备的类例尽同于纪传体。编年体《别录》的
具体做法是把史书内容按下列情况区别:一是分别标出每帝纪中后妃、皇
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