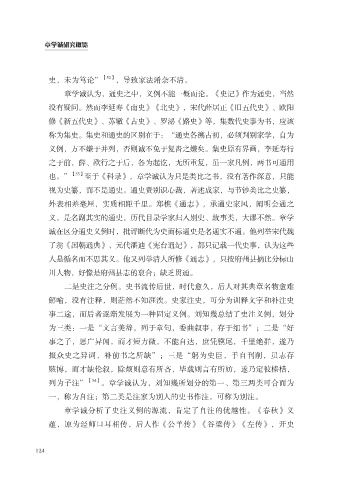Page 132 - 内文
P. 132
章学诚研究概览
史,未为笃论” 【52】 ,导致家法淆杂不清。
章学诚认为,通史之中,义例不能一概而论。《史记》作为通史,当然
没有疑问。然而李延寿《南史》《北史》,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
修《新五代史》、苏辙《古史》、罗泌《路史》等,集数代史事为书,应该
称为集史。集史和通史的区别在于:“通史各溯古初,必须判别家学,自为
义例,方不嫌于并列,否则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集史原有界画,李延寿行
之于前,薛、欧行之于后,各为起讫,无所重复,虽一家凡例,两书可通用
也。” 【53】 至于《科录》,章学诚认为只是类比之书,没有著作深意,只能
视为史纂,而不是通史。通史贵别识心裁,著述成家,与节钞类比之史纂,
外表相差毫厘,实质相距千里。郑樵《通志》,承通史家风,阐明会通之
义,是名副其实的通史,历代目录学家归入别史、故事类,大谬不然。章学
诚在区分通史义例时,批评断代为史而标通史是名通实不通。他列举宋代魏
了翁《国朝通典》、元代潘迪《宪台通纪》,都只记载一代史事,认为这些
人是循名而不思其义。他又列举清人所修《通志》,只按府州县摘比分标山
川人物,好像是府州县志的裒合;缺乏贯通。
二是史注之分例。史书流传后世,时代愈久,后人对其典章名物愈难
解喻,没有注释,则茫然不知涯涘。史家注史,可分为训释文字和补注史
事二途,而后者逐渐发展为一种固定义例。刘知幾总结了史注义例,划分
为三类:一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二是“好
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
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缺”;三是“躬为史臣,手自刊削,虽志存
赅博,而才缺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
列为子注” 【54】 。章学诚认为,刘知幾所划分的第一、第三两类可合而为
一,称为自注;第二类是注家为别人的史书作注,可称为别注。
章学诚分析了史注义例的源流,肯定了自注的优越性。《春秋》义
蕴,原为经师口耳相传,后人作《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开史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