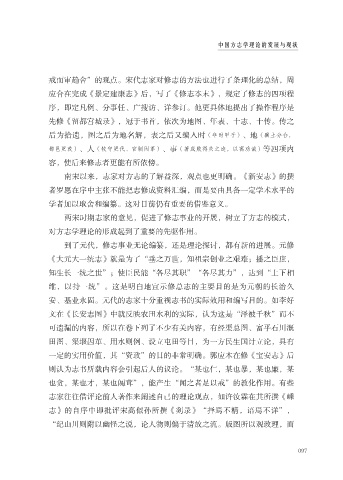Page 105 - 内文
P. 105
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戒而审趋舍”的观点。宋代志家对修志的方法也进行了条理化的总结,周
应合在完成《景定建康志》后,写了《修志本末》,规定了修志的四项程
序,即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他更具体地提出了操作程序是
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依次为地图、年表、十志、十传。传之
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解,表之后又编入时(年时甲子)、地(疆土分合,
都邑更改)、人(牧守更代、官制因革)、事(著成败得失之迹,以寓劝诫)等四项内
容,使后来修志者更能有所依傍。
南宋以来,志家对方志的了解益深,观点也更明确。《新安志》的撰
者罗愿在序中主张不能把志修成资料汇编,而是要由具备一定学术水平的
学者加以取舍和编纂。这对目前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宋时期志家的意见,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开展,树立了方志的模式,
对方志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到了元代,修志事业无论编纂,还是理论探讨,都有新的进展。元修
《大元大一统志》就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
知生长一统之世”;使臣民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
维,以持一统”。这是明白地宣示修总志的主要目的是为元朝的长治久
安、基业永固。元代的志家十分重视志书的实际效用和编写目的。如李好
文在《长安志图》中就反映农田水利的实际,认为这是“泽被千秋”而不
可遗漏的内容,所以在卷下列了不少有关内容,有经渠总图、富平石川溉
田图、渠堰因革、用水则例、设立屯田等目,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具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其“资政”的目的非常明确。郭应木在修《宝安志》后
则认为志书所载内容会引起后人的议论。“某也仁,某也暴,某也廉,某
也贪,某也才,某也阘茸”,能产生“闻之者足以戒”的教化作用。有些
志家往往借评论前人著作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如许汝霖在其所撰《嵊
志》的自序中即批评宋高似孙所撰《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
“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
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