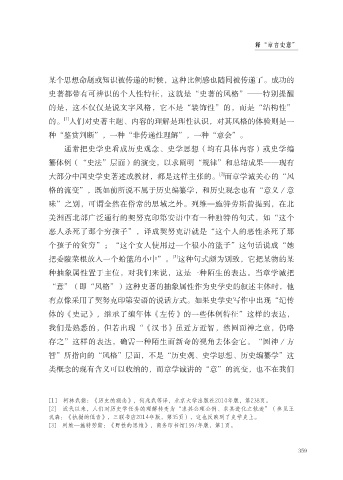Page 367 - 内文
P. 367
释“章言史意”
某个思想命题或知识被传递的时候,这种比例感也随同被传递了。成功的
史著都带有可辨识的个人性特征,这就是“史著的风格”——特别提醒
的是,这不仅仅是说文字风格,它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
[1]
的。 人们对史著主题、内容的理解是理性认识,对其风格的体验则是一
种“鉴赏判断”,一种“非传递性理解”,一种“意会”。
通常把史学史看成历史观念、史学思想(均有具体内容)或史学编
纂体例(“史法”层面)的演变,以求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现有
[2]
大部分中国史学史著述或教材,都是这样主张的。 而章学诚关心的“风
格的流变”,既如前所说不属于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观念也有“意义/意
味”之别,可谓全然在俗常的思域之外。列维—施特劳斯曾提到,在北
美洲西北部广泛通行的契努克印第安语中有一种独特的句式,如“这个
恶人杀死了那个穷孩子”,译成契努克语就是“这个人的恶性杀死了那
个孩子的贫穷”;“这个女人使用过一个很小的篮子”这句话说成“她
[3]
把委陵菜根放入一个蛤篮的小中”。 这种句式颇为别致,它把某物的某
种抽象属性置于主位,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陌生的表达。当章学诚把
“意”(即“风格”)这种史著的抽象属性作为史学史的叙述主体时,他
有点像采用了契努克印第安语的说话方式。如果史学史写作中出现“纪传
体的《史记》,继承了编年体《左传》的一些体例特征”这样的表达,
我们是熟悉的,但若出现“《汉书》虽近方近智,然圆而神之意,仍略
存之”这样的表达,确需一种陌生而新奇的视角去体会它。“圆神/方
智”所指向的“风格”层面,不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这
类概念的现有含义可以收纳的,而章学诚讲的“意”的流变,也不在我们
[1]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2] 近代以来,人们对历史学任务的理解转变为“求其公理公例、求其进化之轨迹”(参见王
汎森:《执拗的低音》,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5页),这也反映到了史学史上。
[3]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