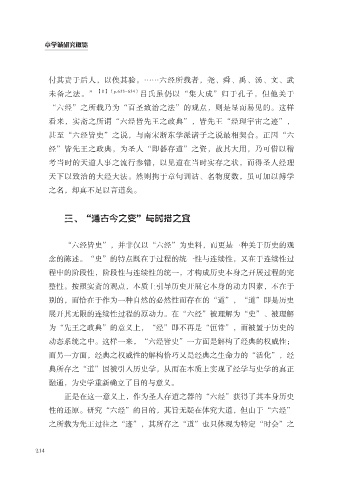Page 222 - 内文
P. 222
章学诚研究概览
付其责于后人,以俟其验。……六经所载者,尧、舜、禹、汤、文、武
未备之法。” 【8】(p.633-634) 吕氏虽仍以“集大成”归于孔子,但他关于
“六经”之所载乃为“百圣致治之法”的观点,则是显而易见的。这样
看来,实斋之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皆先王“经理宇宙之迹”,
甚至“六经皆史”之说,与南宋浙东学派诸子之说最相契合。正因“六
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圣人“即器存道”之资,故其大用,乃可借以稽
考当时的天道人事之流行参错,以见道在当时实存之状,而得圣人经理
天下以致治的大经大法。然则拘于章句训诂、名物度数,虽可加以博学
之名,却真不足以言道矣。
三、“通古今之变”与时措之宜
“六经皆史”,并非仅以“六经”为史料,而更是一种关于历史的观
念的陈述。“史”的特点既在于过程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又在于连续性过
程中的阶段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才构成历史本身之开展过程的完
整性。按照实斋的观点,本质上引导历史开展它本身的动力因素,不在于
别的,而恰在于作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而存在的“道”,“道”即是历史
展开其无限的连续性过程的原动力。在“六经”被理解为“史”、被理解
为“先王之政典”的意义上,“经”即不再是“恒常”,而被置于历史的
动态系统之中。这样一来,“六经皆史”一方面是解构了经典的权威性;
而另一方面,经典之权威性的解构恰巧又是经典之生命力的“活化”,经
典所存之“道”因被引入历史学,从而在本质上实现了经学与史学的真正
融通,为史学重新确立了目的与意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圣人存道之器的“六经”获得了其本身历史
性的还原。研究“六经”的目的,其旨无疑在体究大道,但由于“六经”
之所载为先王过往之“迹”,其所存之“道”也只体现为特定“时会”之
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