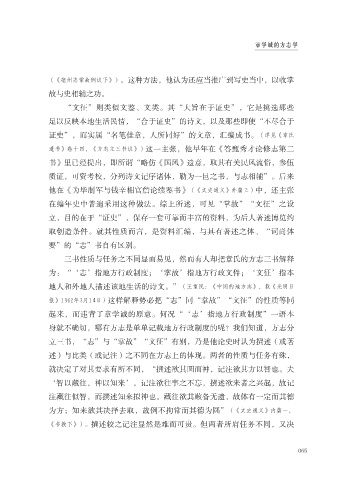Page 73 - 内文
P. 73
章学诚的方志学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这种方法,他认为还应当推广到写史当中,以收掌
故与史相辅之功。
“文征”则类似文鉴、文类。其“大旨在于证史”,它是挑选那些
足以反映本地生活民情,“合于证史”的诗文,以及那些即使“不尽合于
证史”,而实属“名笔佳章,人所同好”的文章,汇编成书。(详见《章氏
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这一主张,他早年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
书》里已经提出,即所谓“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
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后来
他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中,还主张
在编年史中普遍采用这种做法。综上所述,可见“掌故”“文征”之设
立,目的在于“证史”,保存一套可靠而丰富的资料,为后人著述博览约
取创造条件。就其性质而言,是资料汇编,与具有著述之体、“词尚体
要”的“志”书自有区别。
三书性质与任务之不同显而易见,然而有人却把章氏的方志三书解释
为:“‘志’指地方行政制度;‘掌故’指地方行政文件;‘文征’指本
地人和外地人描述该地生活的诗文。”(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载《光明日
报》1962年3月14日)这样解释势必把“志”同“掌故”“文征”的性质等同
起来,而违背了章学诚的原意。何况“‘志’指地方行政制度”一语本
身就不确切,哪有方志是单单记载地方行政制度的呢?我们知道,方志分
立三书,“志”与“掌故”“文征”有别,乃是他论史时认为撰述(或著
述)与比类(或记注)之不同在方志上的体现。两者的性质与任务有殊,
就决定了对其要求有所不同,“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
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
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内篇一,
《书教下》)。撰述较之记注显然是难而可贵。但两者所肩任务不同,又决
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