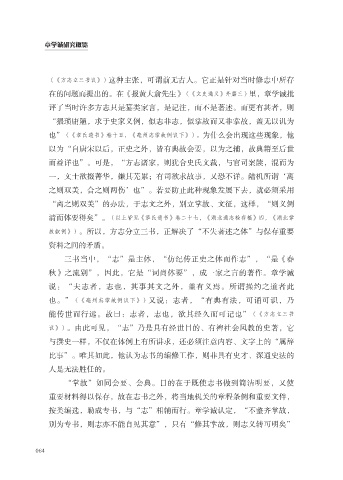Page 72 - 内文
P. 72
章学诚研究概览
(《方志立三书议》)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它正是针对当时修志中所存
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在《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里,章学诚批
评了当时许多方志只是纂类家言,是记注,而不是著述。而更有甚者,则
“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
也”(《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他
以为“自唐宋以后,正史之外,皆有典故会要,以为之辅,故典籍至后世
而益详也”。可是,“方志诸家,则犹合史氏文裁,与官司案牍,混而为
一,文士欲掇菁华,嫌其芜累;有司欲求故事,又恐不详。陆机所谓‘离
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也”。若要防止此种现象发展下去,就必须采用
“离之则双美”的办法,于志文之外,别立掌故、文征,这样,“则义例
清而体要得矣”。(以上皆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七,《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湖北掌
故叙例》)。所以,方志分立三书,正解决了“不失著述之体”与保存重要
资料之间的矛盾。
三书当中,“志”是主体,“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是《春
秋》之流别”,因此,它是“词尚体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章学诚
说:“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
也。”(《亳州志掌故例议下》)又说:志者,“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
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方志立三书
议》)。由此可见,“志”乃是具有经世目的、有裨社会风教的史著,它
与撰史一样,不仅在体例上有所讲求,还必须注意内容、文字上的“属辞
比事”。唯其如此,他认为志书的编修工作,则非具有史才、深通史法的
人是无法胜任的。
“掌故”如同会要、会典。目的在于既使志书做到简洁明要,又使
重要材料得以保存,故在志书之外,将当地机关的章程条例和重要文件,
按类编选,勒成专书,与“志”相辅而行。章学诚认定,“不整齐掌故,
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只有“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
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