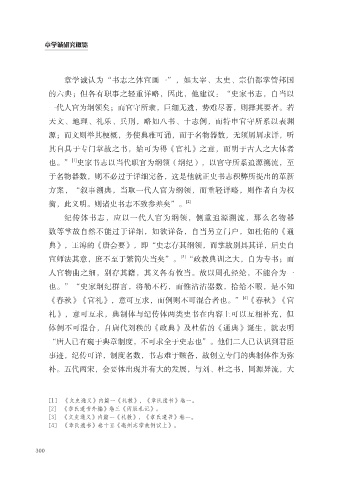Page 308 - 内文
P. 308
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认为“书志之体宜画一”,如太宰、太史、宗伯都掌管邦国
的六典;但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因此,他建议:“史家书志,自当以
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
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
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
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
[1]
也。” 史家书志以当代职官为纲领(纲纪),以官守所系追源溯流,至
于名物器数,则不必过于详细完备,这是他就正史书志积弊所提出的革新
方案,“叙事溯典,当取一代人官为纲领,而重轻详略,则作者自为权
衡,此义明。则诸史书志不致参差矣”。 [2]
纪传体书志,应以一代人官为纲领,侧重追源溯流,那么名物器
数等掌故自然不能过于详细,如欲详备,自当另立门户,如杜佑的《通
典》,王溥的《唐会要》,即“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
[3]
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 “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
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
也。”“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
[4]
《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 《春秋》《官
礼》,意可互求,典制体与纪传体两类史书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但
体例不可混合,自唐代刘秩的《政典》及杜佑的《通典》诞生,就表明
“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他们二人已认识到君臣
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创立专门的典制体作为弥
补。五代两宋,会要体出现并有大的发展,与刘、杜之书,同源异流,大
[1]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2]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3]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4] 《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