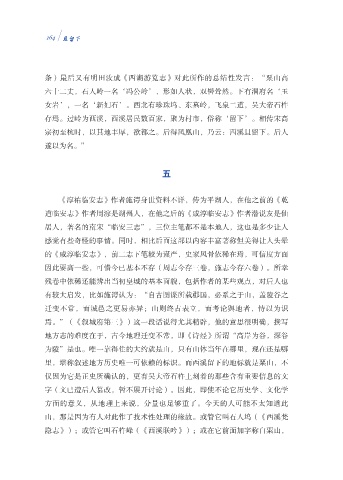Page 174 - 内文
P. 174
164 且留下
条)最后又有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此所作的总结性发言:“粟山高
六十二丈,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形如人状,双髻耸然。下有洞府名‘玉
女岩’,一名‘新妇石’。西北有珍珠坞、东墓岭,飞泉二道,吴大帝石杵
存焉。过岭为西溪,西溪居民数百家,聚为村市,俗称‘留下’。相传宋高
宗初至杭时,以其地丰厚,欲都之。后得凤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后人
遂以为名。”
五
《淳祐临安志》作者施谔身世资料不详,传为平湖人,在他之前的《乾
道临安志》作者周淙是湖州人,在他之后的《咸淳临安志》作者潜说友是仙
居人,著名的南宋“临安三志”,三位主笔都不是本地人,这也是多少让人
感觉有些奇怪的事情。同时,相比后面这部以内容丰富著称但美得让人头晕
的《咸淳临安志》,前二志下笔较为谨严,史家风骨依稀在焉,可信度方面
因此要高一些,可惜今已基本不存(周志今存三卷,施志今存六卷)。所幸
残卷中依稀还能辨出当初皇城的基本面貌,包括作者的某些观点,对后人也
有较大启发,比如施谔认为:“自古图谍所载郡国,必系之于山,盖陵谷之
迁变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异;山则终古表立,而考论舆地者,恃以为识
焉。”(《叙城府第三》)这一段话说得尤其精辟,他的意思很明确,撰写
地方志的难度在于,古今地理迁变不常,即《诗经》所谓“高岸为谷,深谷
为陵”是也。唯一靠得住的大约就是山,只有山体当年在哪里,现在还是哪
里,堪称叙述地方历史唯一可依赖的标识。而西溪留下的地标就是粟山,不
仅因为它是正史所确认的,更有吴大帝石杵上刻着的那些含有重要信息的文
字(文已遭后人篡改,暂不展开讨论)。因此,即使不论它历史学、文化学
方面的意义,从地理上来说,分量也足够重了。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此
山,那是因为有人对此作了技术性处理的缘故。或管它叫石人坞(《西溪梵
隐志》);或管它叫石杵峰(《西溪联吟》);或在它前面加字称白粟山,